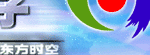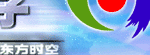|
| 03.27 12:34 |
 |
他是这样看待医生这份职业的
韦加宁:把工作作为一个乐趣,越忙觉得自己越充实,越为更多人做了不少事,你就越愿意做。
他是这样理解病人的
韦加宁:病人来一次不容易,从外地来的,你想他到这儿来,他挂你一个号,他要晚上半夜或者头一天五点钟就睡在这儿,就是为了挂你一个号。
在生命将至的时候,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韦加宁: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干了一生干了自己最普普通通的事情,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觉得很充实。
我们采访韦大夫的这一天,是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的第314天。这段时间里,他已没任何力气再上手术台了。就在这个病房的小餐桌上画了三千多幅手外科方面的手术图谱。在病床前我们采访了他。
韦加宁:这本书就是我在生命的终结以前还能给世人留下一点点的,不叫贡献就是一点点自己的手稿,供他们参考,我就觉得挺欣慰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总是短暂的,你这个人手术再好,技术再高明你总会要消失的,但是你的技术你的经验是会延续很长时间的。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所有的人都不认识韦加宁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年轻学子,会在遇到一个很困难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看见图书馆有过这么一本书,上面有过这样的一个手术,他就会翻开来按着它一步一步就能把那个手术做下来;也许会说我看见过一本书,那画得真漂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加宁的生命就是延续性的。
这是韦大夫自己制作的,因为各种原因致伤致残的手的模型,为了这一双双手能够重新创造奇迹,韦大夫用了41年的时间。1972年,他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同体断足移植手术,之后又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同体拇指移植手术。41年的时间,共做了五万多例手术。这是他工作以来的记录,这些看似平常的病例,记录的是他的态度、职业水准和辛苦。
韦加宁:我画画有基础的,那时自己学点,跟李大夫(韦大夫的妻子)的爸爸学,他是解剖学家,学着画解剖,画画解剖,昆虫这些。盯着看人家是怎么画的,慢慢就会了,就喜欢了,就像很多画家慢慢从小就培训,慢慢就喜欢画画了。
1956年,韦加宁考入武汉同济医学院,五年寒窗,他学业有成也收获了爱情。1961年,他和妻子同时分配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文革期间医院的各项工作陷入瘫痪,韦加宁却利用这段时间,悄悄地继续从教科书中,学着画各种手术图谱。
韦加宁:我们手外科的病人很多是那种穷人,是农村打工的,或者说是很穷的,一般的操作手工业者手外伤很多。这种病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什么经济条件,没钱,他们很无助,一种无奈,这么一个境况,绝望了,也就求你了。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比如说买东西,这个售货员态度差一点,厉害一点,我不买还不成吗,我不吃还不成吗。医生、医务工作者不一样,就求你了,受伤了你说怎么办呢,只有你这儿能治,别的地方都治不好,他到你这儿来治,多少的屈辱都能忍让。
这位生活上完全能自理的小伙子叫张宇,两年前因为登山冻掉了双手双脚,绝望之中,他找到了韦大夫,韦大夫不仅让他的手脚恢复了功能,还鼓励他要大胆地和任何一个人握手。
张宇:在我的眼里,韦大夫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我觉得他像我的一个长辈,每次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到是一个医生在对我说什么,像是一个长者跟我讲一些生活的道理。
这每一封信里,都有一个和张宇一样,从绝望到又开始幸福生活的故事。他们特别愿意告诉韦大夫,自从手被他治好以后,可以结婚了,有孩子了,工作上又取得成绩了。每年,韦大夫都会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贺卡,这其中让他记起了一个蒙古族的小女孩。
韦加宁:她叫斯琴塔娜,很小,她家里的人都是医生,她的手被电烧伤了,歪歪的,很难看,来我们这儿看病。她的家人跟她说,一定要韦爷爷给你做手术,你看看是不是韦爷爷给你动刀子。后来到了手术室,麻醉科给她打了基础麻醉,不睡,再打一针也不睡。韦爷爷,我要看韦爷爷。结果我去了,麻醉科大夫说快呀,韦大夫你过来,她就等韦爷爷呢。打了两次针都不睡觉,一看我来了,韦爷爷,非常满足地睡着了,当时我心里真是…你说一个医生在病人心目中的形象。
这位最在乎在病人心目中形象的医生,现在终于也成了一个病人,这是韦大夫从医41年来,第一次当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人。而且一年前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时候,癌细胞早已在他身上各处扩散了。
韦加宁妻子:我会陪着他,拉着他的手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有我陪着你。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掉眼泪,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好,很舍不得他。
现在,韦大夫画的手术图谱已经接近尾声了,4月份就能够出版了,我们和韦大夫一起期待着。
(编导:蒋文倩摄像:杨帆)
|
|

责编:刘棣 来源:CCTV.com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