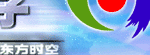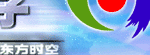|
| 02.13 14:08 |
 |
这里是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今夜在这里演出的是厦门爱乐乐团,乐团指挥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郑小瑛。乐团演奏的作品是一部充满闽西客家风情的大型交响乐组曲《土楼回响》。
郑小瑛:这首很朴素的音乐在龙岩首演的时候听众是三四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他们回到故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一听到这浓郁乡情的音乐他们跟着我一起拍手一起唱。我这么几十年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中国交响乐作品在首演的时候就得到人们这么多的理解和欢迎,当主持人问我说郑老师我们怎么报你的名字,我就脱口而出,我说永定客家女郑小瑛。
当时引起全场的惊奇,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客家人,虽然我们家不说客家话,但是我知道我们客家人的历史,所以这个时候好像一种基因又复活了。
郑小瑛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她195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1960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回国后成为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1989年起任“爱乐女”乐团总指挥,1997年,郑小瑛放弃了北京的一切,奔赴厦门开始了新的音乐之旅。
郑小瑛: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干一点雪里送炭的事情,我觉得北京的艺术团体太多了,有点供多于求了,而厦门一个交响乐团都没有,那里的朋友诚恳地邀请我去,说厦门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的一个风景港口城市,应该有一个现代化的交响乐团,可是厦门没有人懂,所以请我去组建。到了那里以后我发现厦门是一个有很厚的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可以说那里有未开垦的音乐沃土,所以我就同意过去来创建一个乐团,尽管我知道困难很多。
作为一个音乐拓荒者,郑小瑛走进厦门,成为厦门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一个终生沉浸于音乐的老人从此面对的却不再只是音乐方面的问题,为了乐团的发展,郑小瑛不得不为了经费,排练场地,宣传,等等琐事奔忙。
郑小瑛:最难的时候开始要付不出工资了,我真是想一走了之,我觉得一辈子我是干指挥我从来没有负担过这些。但是我一想,这已经三十多个人到了这里,他们都是很年轻的从学校刚毕业的,他们的户口什么都来了,我一走怎么办,有一点骑虎难下。就是为了这已经来了的同志们就是咬着牙这么坚持下来,所以在这里大家都有一种压力,都有一种进取的精神,所以在平常的国营乐队里经常看到的缺席呀、迟到呀这些现象在我那里几乎没有,请假的人也是非常少,大家都很习惯。每次一排练一开始大家都认真投入排练,我们每天都有五小时排练,每个礼拜推出一套新的作品,我决不会说是很轻易的赶快把这个乐团推入市场进行商业的活动,因为要这样做这个乐团就不可能建成一个有水平的交响乐团,它只是不断地重复那些比较浅的、有效果的娱乐性很强的小品,它永远也奏不了交响乐,比较难的协奏曲它奏不了,所以我是按照交响乐的发展的,从开始比较浅然后到比较深,由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小逐渐加大,我一开始只招了三十七个人。
从一开始的37个人,到现在的80多个乐手,厦门爱乐乐团已经初具规模,而通过郑小瑛和乐团乐手们的努力,厦门城市的交响乐素质也慢慢在提高。
郑小瑛:因为交响乐在音乐艺术中它是一个高品味的品种,听众需要有一个培养的过程,我记得刚去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会有一次只卖掉二十二张票,我说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观众那么样的不理解我们,不接受我们。但是到了去年我们曾经达到过就是平均每场有三百来张票,对于厦门这样一个只有五十来万常住人口的一个小的城市来讲就相当不错了。我觉得不是群众不喜欢,而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欣赏。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总是采取一边演一边讲的,他们叫做郑小瑛模式的那种办法,很受欢迎,有的听众都要问,今天有没有郑老师讲,然后才来买票。
5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厦门爱乐乐团在交响乐舞台上逐渐醒目,乐团演奏的大型交响乐组曲《土楼回响》也荣获了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象以往一样,郑小瑛的脚步没有停滞,她的眼光再次望向更广阔的远方。
郑小瑛:我们带着《土楼回响》到日本去演出,受到非常大的欢迎,他们日本人用客家话唱了那首客家山歌跟我们合作,达到了音乐会的高潮。佐士堡的市长连连说伟大、伟大,中国交响乐不可思议,新泻的市长说,我知道中国的交响乐比我们日本要滞后,但是真是没有想到厦门能够有这样好的乐队,而且还有这么好的中国交响乐,所以他们对我们厦门,对中国有一种刮目相看的一种感觉。
今夜,就象重演着在厦门,在永定,在日本的一幕幕,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得到了音乐界和北京观众的欢呼。在离开了5年后,郑小瑛终于再次站在了熟悉的北京的舞台上,感受着人们的尊重。
郑小瑛:英建老师是厦门爱乐乐团的乐迷、大乐迷,她有一个固定的位子,每次她都在那个角落坐。
这是演出后的第2天,明天,郑小瑛和这位追随着她专门从厦门来北京听演出的美国老乐迷就要分开了,郑小瑛将带着《土楼回响》远赴美国排练演出,她要把她的音乐,厦门爱乐乐团的音乐,中国的音乐带到那里去。
|
|

责编:周阳 来源:CCTV.com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