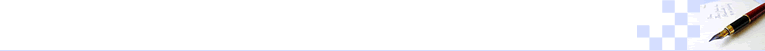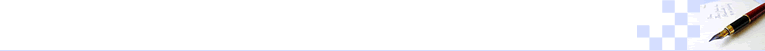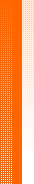|
莫让历史变苍老
——厂庆感言
陈光忠
在上世纪的1983年,为了纪念延安电影团成立45周年、新影建厂30周年,我曾撰文《此爱绵绵无尽期》。
像电影的闪格画面,时光已进入21世纪的2003年了。今天是延安电影团65周年、新影50周年的“红双喜”了。
时间是生命的积累。
我倍感人生苦旅的短促与漫长,生命的坚强与脆弱,岁月的多情与无情,事业的颠峰与低谷……
我在新影工作了三十多年,虽然调到中国新闻社,体验了一阵仕途的迷惘,自己却始终没有放弃影视纪录片的“作业,没有动摇我对纪录片的永远的爱。对新影“母厂”的情结,我始终怀着感激、感动、感慨和感恩之情。
“姜是老的辣”不能一概而论。吾老矣却“长不大”,吾老矣却不老练。如我的自白诗——《无须告别幼稚》:
“从一头黑鬓到双鬓染霜,
无情与有情的时间老人,
同我促膝谈心;
我害怕别人说我‘稳重’、‘成熟’;
我宁愿幼稚,
自己难以成熟。
成熟意味着将失去鲜活,
与熟烂、衰老和消亡同步。
唯有幼稚可以成长和发展,
幼稚孕育着希望与新生。
我
高兴别人说我幼稚,
心灵保留一块纯净与激情的绿土,
青春的太阳永不坠落。”
…………
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
天,面对着耀眼的延安之光,面对着新影“人民电影先锋队”的火红旗帜,面对着中国纪录片人难忘的“节日”,我是肃然起敬地对历史回望,回味与回拜的。更重要是深情地回忆与思考。这也许是我“返老还童”的心态。
在那激情澎湃的五十年代,我们曾经拥有放飞青春的梦,有着率真的性格和单纯的思绪,也有着几分“小资”的浪漫。我才二十岁出头,同伴们都是快乐的单身汉。那时候物质匮乏,生活清苦。我们聚叙在皇姑坟集体宿舍的平房里。大冬天,煤球炉熄灭了,屋内灌着寒风。年纪比我们大些的诗人何钟辛、善于调侃的肖向阳、蹙眉沉思的高仲明……还有我;大家一起谈天说地,谈文艺、谈纪录电影的问题。我们快乐地争论着。我痛快地呼吸着透心凉的空气,让思维与灵魂像洁净的雪花自由地飞舞。至今,我还留恋那“沙龙式”的聚会?可是1954年席卷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却把我们视作“反党小集团”。老何和老肖就“胡风问题”立案审查,我和其他同志受到了批判。我当时感到非常惶惑和震惊。我们只不过围绕着我的一部纪录片《永远年青》的创作问题表述了不同的意见,只不过常常聊到一些文艺观点而已。说真的,我当时连胡风的书一本也未读过,何谈受胡风的思想的“毒害”?在此期间,我的逆反与惊奇的心理驱使自己偷偷地翻阅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和他的一些著作。觉得“主观战斗精神”也有其合理性;胡风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幸亏新影的“反胡风运动”没有如火如萘地展开,我们的政治结论是“组织上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关系。思想受胡风反革命的文艺思想所影响。”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相互吹捧”、是“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结合”、是“落后意识的小圈圈”。我们庆幸总算逃过这一劫。现在回味那段纯情与燃情的“沙龙”活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沙龙”的意义,往往是“人与群分”的艺术探索,是以独立的人文精神体现自己的价值,是对科学与民主的热烈拥抱与期待。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极“左”的思潮对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是有破坏性的;对知识分子的心理、精神以及人格的损害、冲击和压力是很大的。然而,中国纪录片人始终以不倦的敬业精神和执着的使命感无怨无悔地耕耘着、收获着;在前进中留下了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属于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也属于自己的坚定的足迹。
新影是我难以舍弃的红色情结。我们许多人的半生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我们的生命同祖国的命运一起欢与愁、喜与忧、彷徨与反思、伤痛与梦想。风雨兼程的五十年,新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了赢得了今天的变化,从延安到东北到北京几代人没有停止过奋进的步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生活,也记录着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们留下中国命运变化的档案、留下战火纷飞和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档案、留下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档案、留下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的档案、也留下我们每个人的良心的档案。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媒体多元化的竞争时代,难道新影不正处在历史的尴尬之中吗?难道新影不正是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历史吗?
我们铭记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怀旧,纪念历史是为了历史的发现和历史的创新。
历史会变老、会变得苍白,光荣会逝去,辉煌会暗淡;唯有变化才赋予历史的新的生命和新的价值。
现实每天都在成为过去。我们每个人也在写着一部历史。
此时此刻,重弹昔日的荣耀曲调,说些锦上添花的贺词,似乎同逼近的严酷现实的气氛不太谐调。
我还是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话,作为对“红双喜”日子的诚实而真情的祝愿: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2003.5.北京
抗“非典”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