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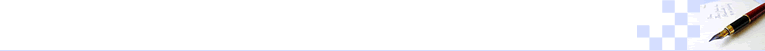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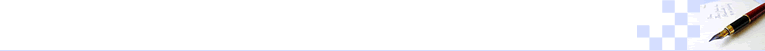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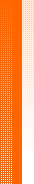 |
|
西藏的历史是西藏劳动人民谱写的,用形象化的影片来纪录西藏人民翻身史的是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忘我精神,就不可能再现西藏的历史。 2001年5月是西藏和平解放50年的日子,也是我们参加新闻纪录电影工作半个多世纪的日子。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50年代开始用新闻纪录电影谱写了西藏的编年史,这些珍贵的历史影片资料就是新影厂上百个摄影师踏遍雪域高原留下的足迹。 从昌都战役到现在,新影厂从来没有间断过纪录西藏重大事件。早在“昌都战役”,在总领队郝玉生的带领下,拍摄了《解放西藏大军行》。紧接着,他们又随进藏部队进军西藏。途中经过连绵的雪山,纵横的冰川,全凭两条腿走过去的。在翻越雪山时,两腿插在雪堆里,靠战友和老乡的搀扶,靠着拉马尾、扒雪往上爬,缺氧、缺粮、缺油盐,使许多战士身体虚脱,他们晕倒了,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将和雪山永存。从甘孜徒步行军2000多公里,走了3个多月,进藏部队胜利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解放,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上。摄影队拍摄完成了《光明照耀着西藏》的纪录片。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雪域高原留下足迹的人们。 不能忘记在进军西藏途中年轻的摄影师关志俭同志因突发高原性肺心病长眠在红军长征路过的甘孜城。 不能忘记在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因严重缺氧而倒在珠峰脚下的青年摄影师石明纪同志。 不能忘记为了纪录西藏人民的新生,在雪域高原留下过他们足迹,今天已离开我们的田枫、李堃、杜宗棣、韩德福、张永生、方振久、董振先等同志,雪域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们。 不能忘记新影厂老一代领导,他们不辞辛苦亲临西藏组织领导拍摄,他们是丁峤、郝玉生、刘德源、赵化等同志。 西藏摄影站是在完成进军西藏之后,于1952年由庄唯(第一任站长)、孔令铎、计美登珠、扎西旺堆、董振先等同志开始组建。当年厂里决定,驻藏摄影师1—2年轮换。第二任站长孔令铎、泽仁。第三任站长赵化,分两个队:扎西旺堆、张发良为一队;王喜茂、赵民俊、陈和毅为二队。第四任站长李振羽、赵民俊。第五任站长赵民俊一人值班。1959年初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当时登山队摄制组的李振羽、王喜茂、沈杰和赵民俊一道共同拍摄了《平息西藏叛乱》影片。接着厂里又派出以丁峤为领队,编导郝玉生、何钟辛,摄影李振羽、靳敬一、杨今勇、陈凯初、方振久、泽仁、赵民俊、计美登珠、扎西旺堆,作曲刘才,录音黄宝泉等同志组成的摄制组拍摄了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强有力地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造谣中伤。影片较深刻揭露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谱写了赞歌。 1959年以藏族摄影师为主体的西藏站开始长期在西藏工作,他们继承“人民电影先锋队”的光荣传统,在雪域高原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1991年和平解放西藏40周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西藏新闻纪录电影回顾展”,老厂长钱筱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病床上为“回顾展”题词:“勤奋拍摄四十年,西藏巨变尽入镜头,驰骋屋脊千万里,解放历程永留银幕。”西藏站的同志们实践了老厂长的期望。我们回顾50年的历程,当初,我们这些贫苦出身的孩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当记者,更没有想过会与摄影机结缘。但是,历史的机遇使我们担负了纪录西藏历史的重任,为西藏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新歌。 80年代以前,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差,下乡大部分时间都搭邮车或大卡车,更多的路靠步行或骑马。在高寒缺氧的环境里,经常背着几十斤、上百斤的器材以及吃、穿、睡的东西。特别在阶级斗争较复杂的年代,下乡人身完全没有保障,只有“把脑袋挂在裤腰上”,夜晚睡觉轮流值班。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作战中,我们同八一厂的同志们并肩战斗。在战场上,我站赵民俊、泽仁同志负伤,次登同志荣立三等功,计美登珠同志在炮火中抢救战友,传为佳话。 几十年来,西藏站的同志,长年在雪域高原东奔西走,家中的事很少过问。记得1962年国际反华势力大合唱,印度扩张主义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沿海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北方“苏修”也蠢蠢欲动,当时国内又遇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有力地反击了反华大合唱。新影厂当时组成东、西、北三个摄影组,跟随人民解放军拍摄和纪录了这段历史。 西线首先派出田枫、任太华、计美登珠、泽仁去中印边界最紧张的阿克钦(西藏、新疆交界处)地区。这里地处世界屋脊的屋脊,是一个不毛之地,但是战略要地。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采取蚕食政策,我军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当时这里只是边境上磨擦,我们拍了一些资料。中印边界西线紧张局势相对缓和一些后,我们就回前线指挥部接受新任务。 1962年8月厂里调我和计美登珠回北京另有新任务。到北京后,厂里叫我们去西藏。当时我俩的家属,卓玛和央京系西藏派往新影厂学习剪接、编辑,参加了《西藏简报》的工作。因1962年全国各地方厂下马,西藏更没有条件办厂,西藏文化局决定调卓玛、央京回西藏工作,厂里要我们把家搬回西藏。当时我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计美登珠有两个,一个不到两岁,一个不满周岁。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再由兰州转火车到柳园,再从柳园搭部队的卡车去拉萨。因搬家,每家都有锅、碗、瓢、盆、睡具、用具,加上孩子又小,又要经过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孩子、家属们的高原反应,水土不服,困难重重可想而之。行车20多天,才到拉萨,拉萨我们又没有家,只好打地铺住在摄影站的办公室。但到拉萨第一天,中印边界中段前线告急,站里的赵民俊、次登二人已上前线了,我和计美登珠到拉萨第三天就出发去前线了。爱人和小孩根本没有时间安置,只能由她们自己去处理吧!想到这些,我们的家人是多么可敬可爱,她们从没有怨言。计美登珠有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其他的同志都是两个三个。夫人们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在身边,都是她们自己照顾自己,我们没有尽到父亲的义务和责任,是有愧的,我们功劳的一半当然是她们的。 西藏站的同志们坚守自己的岗位,从来没有失职过,西藏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被摄入镜头,在那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站的同志更加焕发了青春。这段时间里,我站先后拍摄了《故乡行》、《绿色的墨脱》和《我们的家乡——西藏》系列片;还拍摄了《沸腾的拉萨》、《祈祷大法会》、《藏历土龙年》、《世界屋脊的传说》、《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西藏今昔》、《雪域春曲》、《拉萨雪顿节》、《拉萨一人家》、《喜马拉雅—山谷》、《雪域秋曲》、《维修中的布达拉宫》、《班禅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走过的日子》、《拉萨的韵律》以及代制片《拉萨》等影片。这十多年是西藏站的同志们丰收的季节,是向新闻纪录电影战线上曾经辛勤培养我们的老前辈们的回报,也是向西藏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答卷的年代。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早在中印边境战争后,文化部对我们通令嘉奖;敬爱的周总理亲临新影厂接见前线摄影队,接见了我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先后数次授予我站先进集体的绵旗,并荣获“珠穆朗玛文艺金奖”先进集体的称号,也获得了国家级“华表奖”先进摄影站。 回忆过去,我们记忆犹新,新影厂上百位摄影师、编导和其他工作人员在雪域高原留下的足迹,永远述说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