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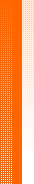 |
|
当我端起摄影机的时候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芦沟桥制造事端不久,我以西北电影公司战地记者的身份,同来自上海的著名新闻记者沈逸千、余创硕等一起,从太原出发上前线去。当时,我们步行到了繁峙、沙河一带,已经听到从前线传来的隆隆炮声。一路上见到了数不清的伤兵,有一股败兵,拿枪对着我们的胸膛,就在光天化日下,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物一抢而光。 正当走投无路时,我们遇到一支开赴前线的八路军。看到我们的狼狈相,得知我们的遭遇,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支军队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才真正是民族的希望。 我返回太原时,西北电影公司正忙于搬迁到成都去。但我决心参加八路军。谁知,我一次又一次向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提出申请,却又一次次被婉言谢绝,说是八路军还没有条件搞电影。我决心在八路军里当个兵! 过了几天,我又跑到办事处,接待我的仍是那位和蔼可亲的赵品三同志。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我们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要接见你。你可以和他谈谈。”接着,他把我带进一个小院,我见到有两个同志正站着谈话。经赵品三同志介绍,知道一位是周恩来副主席,一位是叶季壮同志。我向周副主席简单地说明了为什么不愿去大后方而要求参加八路军的心愿。他爽朗地笑着对我说:“好啊,好啊!你的情况,品三同志都向我说了。你有那么大的决心,要参加我们这个队伍,我们欢迎嘛。”他问我是哪里人,搞了几年电影啦?我说:“老家浙江,搞电影有四年了。”他说:“这就有点手艺了嘛。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所以还顾不上搞电影。不过我们总会有办法把电影搞起来的。因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许多朋友,都很想了解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活动情况,很想看到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绩,而电影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现在你可以先到前方去,同战士们一起过过战地生活,看看前线的战斗场面。即使不参加作战,听听枪炮声也好啊!”当时,我是含着眼泪聆听着周恩来副主席的每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从此,我就成为光荣的八路军的一名战士。 第二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带着伊文思赠送的“埃姆”摄影机来到延安。我军第一个电影团体——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建立了。当时我也立即由抗大调来工作。 1939年,我和电影团的同志们,为拍摄大型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准备上前线去。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我们。 那天,我们到了杨家岭,毛主席在窑洞前把我们迎进了门。这是主席办公的地方,墙两边挂满了军用地图,中间有一张方桌,几条长板凳和一只取暖的木炭火盆。靠窗是一张用几块木板钉成的办公桌,桌旁有一个书架。毛主席看我们都站着张望,觉察到我们很拘束,就招呼我们坐下,象拉家常一样向我们问寒问暖。问我们在延安生活过得怎么样,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主席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习,还劝我们认真读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主席循循善诱的谈话使们感到他如同亲人一样。袁牧之同志向主席汇报到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时,毛主席说:目前情况看来是这样,但这是暂时的,形势总会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拍摄很多的电影。譬如,现在去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不可能,但过几年,你们就可以去拍了嘛…… 毛主席的话使我们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心,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广阔、光明的前景。我们带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奔向了抗日前线。 我们冒着初春的寒风,渡过滚滚黄河,到了华北抗日前线。在三八六旅攻打榆社城的战斗中,我拍了许多片子。那天,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有大炮和机关枪。我要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地段,到另一个突击点去,陈赓同志不准我去冒这个险,因为在这个突破口牺牲了我们许多战士。我偷着带一个通讯员,一鼓作气,弯着腰,飞步冲过了敌人火力最密集的封锁区。我还没有喘过气来,近的、远的冲锋号震撼着大地,战士们象插翅膀的猛虎,向敌人的一个大碉堡扑过去。有的战士竖起云梯搭在碉堡上,有个战士背了一串手榴弹爬上了云梯,把手榴弹向碉堡里投掷。敌人仍在顽抗。有的战士负伤下来了,但有更多的战士在急促的冲锋号下,在高昂的喊“杀”声中猛冲……我冒着弹雨把这些火与血、生与死的场面拍到电影机和照相机的胶片上。 我看到几个战士夺到一门平射炮,我正要用摄影机拍摄,一个炮弹落在附近,我被炮弹震倒在地上,昏迷了。有几个战士来抢救,把我弄醒了,我看到周围死伤了好几位战士。我只是震昏了,没有受伤,我又拿起摄影机拍摄了这个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