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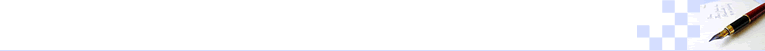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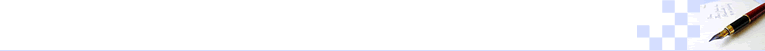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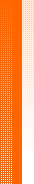 |
|
走近红墙 人生会有许多理想,而理想多是华而不实。我少年不敢奢望,只求一个温饱。因为我的家乡苏北太穷了。 往往运气又会不期而遇。当我只身远行千里到北京报到的时候,我既没有范进中举的疯狂,也没有周瑜赤壁的得意,反而有些自卑和胆怯。在人地两生的北京,一个操着浓重苏北口音的男孩,如何生存和生活。 北京容纳了我。新影同志们的热情融化了我。把我当作他们的晚辈和后生。 经过1959年寒冷的冬天,60年代第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个春天,我和老同志一起去西郊四季青公社拔大白菜,去东北旺围猎黄羊,到门头沟煤矿下矿井,在二龙路街道拍邻里之间,也跟随去首都剧场拍摄苏联芭蕾舞台艺术,还去摄影棚观摩见习拍摄《风暴》和《早春二月》。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工作是繁重劳累的。 从严冬走向早春,我经受了第一个考验和锻炼。在北京春节的时候,虽然那时的积雪还没有融化,但我已经感到春天的温暖。那一年的春节,许许多多的老同志邀我去他们家里过年,热气腾腾的饺子和辛甜的腊八蒜,使我感动得流泪。 吃百家饭的孩子好养。这一年我就是吃百家饭过了春节。组织和同志们的温暖感动了我,也教育了我,使我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春节刚过,摄制工作室的秘书王宪林通知我,说主任要和我谈话。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主任办公室。石益民和杨今勇坐在那里,我怯怯的,他们热情地要我坐下。石益民同志却站了起来,郑重地和我说:经过几个月的观察考验,正式分配我去中央队工作,做摄影助手。 杨今勇对我说:看到我们“人民电影先锋队”那面旗帜了吧,这就是我们中央队的光荣。小伙子,好好干吧。到中央队去工作不容易,首先是听话守纪律;二是肯干能吃苦;三是爱学长进步。 我记住了,默默地记在心里。我依然那样,既没有过我的兴奋,也没有过多的惊喜。我知道随中央首长工作,不能出差错。 然后我到中央队报到。中央队当时就在我们马相胡同宿舍。虽然不是单独一个院子,但也十分清静和安全。虽然院子里住了那么多的住户和单身汉,但很少有去办公室做客的,因为这里的工作需要严格保密。 我的老师就是庄唯、舒世俊、张贻彤、陈锦俶几个人。应该说我沾了年龄小的光,再加上乡下来的孩子天性老实,他们都喜欢我,把我当作小弟弟对待,亲切热情,关怀备至。虽然我在扬州艺校学的新闻电影,但那点理论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用的,还是从实践开始,擦机器、装胶片、倒片子、作记录、收拾屋子,样样都干。 万事开头难。老师们对我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们也是从这基本功开始的。 助手就是助手。尤其在中央队工作,不能出一丝一毫差错。中央来的电话要详细记录,时间、地点,哪位领导活动,接见谁,记录不能有误。虽然当时还没有允许我到现场工作,但听到毛主席、周总理、刘主席的名字已够亲切的了,好像已经接近他们。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60年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幸允许摄影助手到现场工作。 现场就是人民大会堂。开幕那天我换了一身新洗的布衣服。虽然天气已经开始转暖,但那时候我买不起毛衣,只好里面穿了一件棉背心,现在想起来够寒碜和脸红的了,但那时我确实就是那样。 到了现场,我帮助老师支好三脚架,摆好机器,然后安排我的工作位置就是在大会堂西南角的舞台下,我的任务就是装片子。从大会开始到大会结束,我的两只手就闷在黑口袋里,一盒一盒换个不停。那时的摄影机是西德的“阿莱”,一个片盒只能装200呎片子,任其拍,机器转两分半钟即完。同期声的机器是大片盒子,也就是装400呎。当时在现场工作的摄影师很多,我一个人负责帮助那么多摄影师换片了,工作量大,又不能出差错,大会堂的暖气又足,热的我满头满脸都是汗,小棉背心也湿透了。等我工作完了,第一次开幕式的会议也就结束了。 虽然就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下,紧张的工作和紧张的心情使我不能走神,可惜我没有仔细地看到毛主席、周总理,甚至于连谁作的报告我都没有听清楚。 散了会的大会堂空空的,服务员们忙着收拾茶杯椅子,记者们忙着收拾三脚架和机器。我心里茫然的,这个时候我才感到后悔和紧张。 唉,我在毛主席的跟前,却没有没有看见毛主席。我心里还惦记着我装的胶片有没有毛病,出没出差错。 过了一天,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师给我的机会,让我确确实实的看到了毛主席。 第二天举行全体大会前,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会见一些代表。舒世俊和庄唯布置我背着两个片盒、搬着一个小板凳跟着他们。片盒是装满片子的,随时可以用,小板凳是我们从食堂里带过去的。为老师站着拍高度。 先到118厅,那里是中央首长集中休息的地方。我怯怯的,一身农村孩子的打扮,又背着那么多东西,很是好笑。不知什么地方该是我的位置,我只好站在门后。大会堂保卫科的张科长走过来看看我的胸牌,严肃地问:谁带着你到这儿来的。我不知所措,顿时害怕起来,不知他的官有多大。舒世俊赶快过来对他说:不要欺侮人,看我们小是怎么的。老舒和张科长是老朋友,这半是玩笑半是责问的口气,解救了我。在场的几个服务员也笑了。 不一会,毛主席进来了,高大的个子从我身边一走而过,像带着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带笑迎出来握手。我也跟着摄影师挤过去,跟在舒世俊的后面。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遥远,各种感情一齐涌上心来。不错,我就站在毛主席身边,他就是毛主席。 我们的救命恩人呀。我后来老后悔,在我到北京来的时候,父亲曾说过,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要向毛主席磕个头,谢谢他。怎么我这次竟忘记了呢? 没有想到,我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孩子,从此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其实说从此,也是个虚词。不过自我得意安慰罢了。后来毛主席单独见外宾的时候还是不让助手去。我仍然默默地为老师装片子,就这一点,我已感到心满意足了。 一个多月以后,机会又来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访,先是周总理迎接会见、宴请。来访的第二天蒙哥马利又去天津杨村参观我军的空军基地,这些我都有幸参加了。在杨村基地蒙哥马利由周总理陪同,还一起吃了战士们做的热豆腐。 蒙哥马利毕竟是军人出身。检阅部队的时候,他让战士把帽子摘下来看看。他说,摘了帽子更看出中国士兵的神威,怪不得朝鲜战场取得了胜利。 带着在杨村看到的战士神采,蒙哥马利要去拜望毛主席。 1960年5月27日,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随舒世俊第一次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我想又能见到毛主席,心里是极大的兴奋。4月份我和舒世俊去大会堂接见厅拍摄周总理接见外宾时,我又让张科长批一顿。那时我穿一双乡下的布鞋,干干净净,我已感到满足了。可是张科长却走到我跟前说,新来的不懂规矩吧?你能穿着布鞋进大会堂吗?布鞋是民族服装,只有领导人和外交官才能穿民族服装见外宾。 当然我记住了。后来我去百货大楼买了一双皮鞋。当时我的工资少,皮鞋贵,买不起,售货员拿了一双处理品给我。虽然是一个厂子,一个牌号的鞋,外表一样,里子却不一样,但穿起来,外观也看不出来,价格便宜,我买了。这次到丰泽园见毛主席,我就穿这双鞋,还高高兴兴的。 但乡下人就是乡下人,再加上我的一边倒小平头,就露出了马脚。进了丰泽园又过了一个院子,到了颐年堂。院子里干干净净,绿草茵茵。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在那耸天的大树下谈话,看到我随着舒世俊过来了,他拿着烟笑着对舒世俊说:小舒,你今天把小弟也带来了啊?舒世俊马上报告说:他是我的助手,新来的,中办批准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笑了起来,从亲切宽容的笑意中,可以体会到当然是批准的,否则乡下娃儿能自己跑到这儿来了? 见到毛主席,又是那么风趣,起初我以为要把我赶出去,毛主席一说一笑,我放心了,心里甜滋滋的。说着,蒙哥马利来了。毛主席上前去迎接,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一是口音不懂,二是心里胆怯。我和舒世俊在颐年堂会客室拍了一会儿,就退出来了。 丰泽园,红墙里面的红墙。颐年堂,深入红墙里面人们向往的地方。青砖灰瓦,红檐绿窗,鲜花高松,这都是我后来才逐渐感觉到的景象。见到毛主席的当时,我真的没有顾得及去欣赏这美丽清幽的庭院。 从此时此地,是我迈出新的一步。从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老机场,如此重复的日新日复,我一直干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溘然辞世。我含着悲哀、伤痛而又依依不舍的心情,最后一次参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拍摄亿万人民悼念毛主席。9月15日我含着泪,给毛主席遗体三鞠躬告别。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又随同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在他们身边工作,一直到我依依不舍地离开记者工作,走上部门领导的岗位。前后经历了三代领导人,30个年头。 中南海的红墙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象,我走进了她,却又感到很少的了解她。多少花开花落,春夏秋冬,红墙,我只是走近你。永远向往。 此时,我突然想起1971年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时候,毛主席说过,不能忘记我们的朋友,是他们用轿子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我不该忘记的朋友太多啦,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竹林近水半边绿,桃花连村一片红”。我永远怀念和铭记给过我支持、指导、帮助和教育的前人长辈,同行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