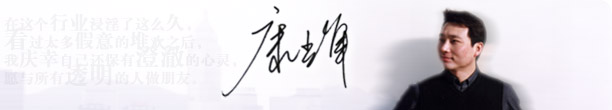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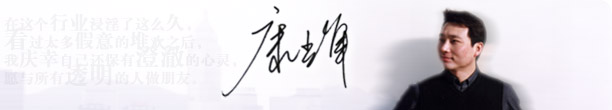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
|
清晨那张温暖的笑脸
“我喜欢固守于自己的天地中”
小时候的康辉是一个“很拧、很任性的人”。康辉“拧”的表达方式是表面上妥协,但却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小时候,康辉和姐姐觉得幼儿园太闷,就逃了出来。被父母知道了,免不了要被说一顿。姐姐是错就错了,就这样,也不承认她错了。康辉是你说我错了,我就说我错了,但实际上内心并不认错。“我想我可能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小时候,老师总是把我当成好学生,而且他们在表扬我时,想当然地将很多他认为是好学生的准则套在我的身上。很多老师给我塑造了这个形象,我也不和他们澄清反驳。”那时常有所谓“好”学生帮助“差”学生的活动。老师把康辉和两个所谓差生安排在一起。康辉也不知道如何去影响别人。“在我的概念中根本没有认为他们是差生,需要帮助。却往往能在他们身上发现很多的优点,甚至认为他们很多时候要比我强得多。”
康辉在初中、高中的6年时间里都是很封闭的。“我把自己包裹的很严实。过了十一二岁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再蹦蹦跳跳的就很幼稚,而应该皱着眉头思考问题才是应该的,用现在的话说要很‘酷’的样子。有时候人的性格变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我上初中一下子就变得很内向、寡言了。”
虽然从小说当班干部一直到大学一年级,但康辉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有的人比较擅长也乐于和大伙儿聚在一块儿,我却比较乐于固守自己的一个天地。表面上看我这个人很蔫,尤其在我读中学时。但我自己觉得我的内心世界很丰富、敏感。那时我就看一些书、小说,经常沉浸于一个幻想的世界中,我能给自己幻想一个和周围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也有喜怒哀乐,我很陶醉其中。”
康辉从小就很喜欢电影。对电影有种迷恋。一直到现在他还认为电影是一个做梦的东西,让你把周围繁杂的一切抛开,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且康辉什么电影都愿意看,灯光一黑下来,似乎就进入自己的世界。
“初中二年级,我一个人跑去电影院看豫剧的戏曲艺术片《对花枪》,是老生、老旦戏。但我依然看得很投入,很入迷。电影是特别让我喜欢的一件事情。”“小时候最喜欢看的电影是《流浪者》。其实看不太懂,但固执地认为时间长的电影要比时间短的电影要好。后来又看了很多遍。”
康辉的印象中,小时候的文化生活要比现在丰富得多。父母常带他和姐姐去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芭蕾、民族舞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话剧、石家庄地方戏等等。那时的他也看不太懂,但说不上为什么就是爱看,而且能从头看到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父亲带他和姐姐去看河北梆子戏,是一个特有名的传统戏《蝴蝶杯》,一整本唱下至少要3个小时。当时大他两岁的姐姐根本就坐不住,不是睡觉就是乱跑,而康辉坐在那儿从头看到尾。到现在,康辉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那么感兴趣?那么有耐心?
小时候的康辉甚至还动过去学唱戏的念头。但长大后,“一来家里人没有这种意识,二来上了初中后自己的兴趣也就转移了。”
初中毕业时,康辉的成绩是全市前5名。当时石家庄一中是全省重点,康辉上的师大附中是市重点。但师大附中的文科是全省有名的,而康辉拿定了主意要上文科。
“父母对我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会干涉。他们对我做人方面的影响很大。”康辉坦陈,与父母的沟通不是很好。父母都是学邮电的,又是很传统的人,认为只要照顾好孩子的生活就行了,不大重视思想上的交流。但康辉认为“父母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直到现在,康辉认为,自己是个真诚的人,也从不算计别人,坚信不管社会怎么样变化,自己掌握一种技能是最根本的,不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去刻意做一些事情,搞好关系。“其实搞好关系也不是什么坏事,与人沟通也是生活的一种技能。但我在这方面不行,也做不来。父母就是那种在工作上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人,而不是靠其他的一些手段。”
康辉有什么事情不一定和父母说,但一定会和大他两岁的姐姐说。在康辉的印象中,姐姐像一个“小妈妈”。父亲经常出差,母亲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照顾他们,于是交给姐姐的任务就是带好弟弟。康辉小时候就像姐姐的跟班。有什么话,康辉也愿意和姐姐说,“我从小就是个被保护的孩子。”
上广院对康辉来说也是件偶然的事情。上了高三康辉才开始考虑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决定考广院,也是源于姐姐的一个在广院念书的同学。他向康辉大肆描绘了一番自己在广院上的电视编导专业。这对康辉来说无疑是个诱惑。康辉从小就喜欢电影,对电视也同样感觉好奇。康辉高考的那年正好赶上北广电视编导专业没有来招生,但有播音专业。在这之前康辉并没有和朗诵沾过边。当时就是想试试,“成不成都无所谓,反正多一个选择嘛。”
去考试时康辉才发现与自己想象的完全不同。那时广院委托省广播电视厅招生,不仅人多,而且考试的人还很不同:男的都西服革履,女的则都化了妆。康辉心里觉得没戏。当时康辉自己准备了一首诗,还精心配了段音乐。进入考场后,康辉问考官:“我能给诗配段音乐吗?”考官一听就乐了,说不用了,你念诗就行了。不过,考试的诗他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自己给配的音乐是一首很著名的吉他曲《阿尔汗布拉宫的回忆》。后来康辉参加复试时没有准备要录音的东西,好在那时课本里有很多需要背诵的课文,于是挺投入的录了一首柳咏的词《雨霖铃》。虽然康辉对自己对家里人都说去试试,但考完之后,就有一种需要别人承认的心态,哪怕考上后自己不去上也行。
当时所有的老师都不支持康辉,他们都有一个概念:播音是不用学的,只要普通话说得标准的人都可以做这个。康辉当时的功课还行,很多老师认为他应该考一个更好的学校。只有语文老师比较赞成,觉得这个职业挺好的,还可以接触很多方面的事情,让自己的眼界开阔。与康辉同去考试的还有一位平时很活跃的女生,很多人就觉得康辉没戏,甚至有个同学当康辉的面说你绝对考不上。康辉很生气,于是,语文老师的鼓励加上这个同学的否定,两个因素让康辉觉得非考上不可。康辉高考的分数线已经过了重点线,当时人大、北大都可以上。康辉是那年广院文化成绩最好的学生。很多不支持康辉考广院的老师觉得康辉很“可惜”。但康辉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后就觉得这个专业挺好的,“我希望我成为播音员,希望自己能在《新闻联播》里出现。”
刚上大学,康辉就经历了一段比较痛苦的语音纠正和训练。上完语音课,“都觉得自己不会说话了。”语音课要照着舌位图去说,康辉自认为从小普通话还行,可上学后发音好象全不对,其他的同学似乎很轻松就过关了,而自己要一点点去纠正。康辉说,“我都不想上了。但很多东西在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突然改变过来了。似乎一夜之间就豁然开朗了。”到第一次专业考试时,康辉得了播音系的语音最高分。这件事情让康辉对自己有了自信。
大学一、二年级的康辉延续了中学的那种比较封闭的状态,似乎还是比较“蔫”。一直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偶尔有机会才能让自己“爆发一下”。现在康辉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大学一年级的一门选修课《莎士比亚剧作导读》,学期快要结束时,老师让我们自己在课后自由组合,每人准备一段莎士比亚剧作的对白。那时同学之间还不是很熟悉,突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展示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大学都很有兴趣。
当时班里另一个女同学找到康辉,想和他朗诵《哈姆雷特》中的一段,哈姆雷特指责他的母亲背叛了父亲与叔父在一起。这段戏的情绪很激烈。康辉自己都想象不出来自己是否可以那么强烈地去表达这个角色。当时因为是第一次考试,大家都憋着股劲,特别认真地准备这段戏。
“我记得当时和这个同学到学校的核桃林去排练。当时天都黑了,我们演完都没有说话,沉默了十多秒钟。但感觉特别好,我们互相都觉得达到了我们认为最好的程度。这时,黑暗中传来鼓掌声。是我们的一个师兄。他正好路过,听见我们的对白,觉得很棒。然后还鼓励了我们几句。”
最后汇报的时候,康辉得了很高的分数。“那一次真是感觉自己这么深地进入到一个角色里去创造,人似乎真的化身为哈姆雷特,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调动了起来。我喜欢自我陶醉,这对你去体验一个东西很有帮助。真让我去演戏,可能我缺乏技巧,但我相信我会体会得很好。我从小喜欢电影直到现在,这是唯一一次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演员那样去体会如何创造角色,它让我有种满足感。”
“发声是个技巧,但真正在实际工作中,能帮助你的不是这个技巧而是更深的一些东西。”康辉认真地说。很多人对播音有误解,觉得播音没什么可学的,不就是念字的吗?普通话好一些的人都可以做这事。“做一个好的播音员必须要有很多的创造在里面。同样一段文字,一个好的播音员和一个差的播音员传达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很多的不同。放到一起一比较,很容易就能分出高下。”
对时下很多的观念康辉特别不能理解。很多人认为播音员地位低,而主持人的地位则是高不可攀的。播音员是念别人的稿子,是传声筒;主持人是自己说话,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很多的主持人,从事的工作和播音员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康辉委屈地说。“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仅仅是你给我一篇稿子,我把它念完就完了那么简单。我工作的8年当中,我觉得从编辑的意识或是对一个新闻工作事实的判断也好,这8年中我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播音员主要任务是去传达别人编辑、采写的东西。主持人是用更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去表达一些想法。而现在有一些很有名气、很红的主持人,工作状态也无非是拿着编辑准备好的东西念一下而已。”“主持人和播音员这两个工作有交叉。但现在很多观念非要生硬地去分开它们。固执地认为主持人比播音员的位置高。这对工作没有任何的帮助。只能造成一些障碍。”说到这些,康辉情绪颇为激动。
康辉觉得自己“真正享受工作乐趣的时候很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大学时的“哈姆雷特”开始,觉得从事跟语言有关系的工作有乐趣。
工作后,在所有的直播节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香港回归的那次。那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做解说。大家看不见他,但能听到他的声音。但刚开始,康辉并没有意识到工作有多么的重要。当时康辉到香港后的情绪并不是很好,觉得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并不是那么重要、情绪比较低落。康辉记得给女友打电话时还掩饰不住自己的低落情绪,觉得自己的工作对整个直播“无足轻重”。但当天晚上直播结束后的一刹那,康辉觉得前两天那种不好的情绪烟消云散了。“能参与进来就不错了,全世界的华人此刻听到的都是我的声音呀!”那一刻,康辉觉得这个工作带来的那种乐趣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还有一次康辉做了一个关于天象奇观的直播节目,彗星和日全食同时出现,是个千年可能才遇上的天象。那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各个地方设立不同播报点报告直播,北京设立一个总演播室,演播出来调度各个播报点。当时央视第一次以这种形式来做节目,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香港回归做一个预演,希望在技术上还是节目整体操作上预先演习一遍,如果成功,对香港回归是个促进。康辉是春节才得到的通知,距离直播两周左右的时间,当时他的压力是挺大的。但康辉的压力并不是来自于这个节目,而是来自自己的压力——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带两个嘉宾做节目,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节目:时间是长达两个小时的直播,内容是距离自己那么遥远的天文方面。康辉开始查资料,与嘉宾反复交流……
之后,康辉担任了一系列节目的直播工作:98年三峡船闸开通仪式、99年天安门50周年大庆、99年穿越天门山特技飞行、2000年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海APEC会议等等。
1999年穿越天门山特技飞行表演中,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龄比较大的搞特技飞行的老同志,平时不太说话。但康辉事先和他沟通得很好,到了直播那天,那位嘉宾发挥特别棒,妙语连珠,非常乐意帮助康辉把节目做完。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K会议,是康辉做的所有直播中最头疼的一次,3天之中做了7场,而且最没有什么规律、变化最多。幸亏和嘉宾交流得很好,最后大家都很满意地做完了节目。
每一次的直播节目康辉都能体会到工作的快乐,尤其是带着嘉宾一起做节目。康辉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我最有体会的是在节目中如何与嘉宾接触、沟通,很多时候,我们变成了像朋友一样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的状态就不再是工作了,而成了你和他们之间的自然交流。这样的状态是一个特别舒服的状态,因为这时嘉宾会主动积极地向你介绍地所知道的东西,你不用太多地去调动他们。”
从“播新闻”到“说新闻”
电视中康辉给观众的印象颇为谦和、稳重,绝无一丝“霸气”。认识康辉是在新版《东方时空》开播的第一天。那天,康辉是最早走进化妆间的主持人,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足有半个小时。他说自己实在是睡不着,“挺紧张的吧?”我试探着问。“的确有点。”康辉老老实实地回答。
康辉坦言,自己进入新版《东方时空·早新闻》是个特别自然的事情,毫无“神秘感”。当时,新闻中心正好要对《早间新闻》动一次“大手术”,康辉从开始的第一版样就参与了。“那会儿,我们尝试了各种形式,制作样片全部是利用业余时间,并没有想一定要到《东方时空》来当主持人。”康辉平静地解释,“因为我在《世界报道》里做得比较稳定,虽然没什么大名气吧,但自己还是挺满意的。起码,我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康辉去新版《东方时空·早新闻》是改版前不到一个月才定下来的。但直到新版《东方时空》开播的前一周,康辉还在《世界报道》节目组值班。最后一次主持《世界报道》时,康辉百感交集。这个节目毕竟是康辉从1994年进入CCTV至今主持的唯一一档节目,一干就是6年哪!“这些年,《世界报道》锁定了相当一部分的固定观众,真要离开还有点舍不得。”康辉认真地说。当康辉向值班编辑提出要向观众说句告别的话时,编辑无能为力地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央视没有“告别”的先例。所有的“告别”方式就是默默离开。
我感兴趣地问:“假如真让你说,你的告别语会是什么呢?”
“我不会说一些特煽情的话,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吧。以前观众都是在工作了一天后,在很短时间里听我讲一些国际上发生的事情。从下周起,我会在早间继续我的节目。总之,就是想郑重地道一声谢谢。”讲这番话时,我发现康辉说得很动情。
在谈到主持新版《东方时空·早新闻》的感受时,康辉只说了一个字——累。我希望他能讲得更具体些。“我个人认为,如果一直这样疲于应付每天的播出,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这种累是生理上的疲乏,跟投入地去做一个自己喜欢的片子的感受不一样。那样虽然也很累,但内心会得到一种满足。比如跑步吧,你会大汗沭漓,也同样会感觉到身心的愉快,很舒服,很痛快。现在累了之后,只想倒头大睡。”康辉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康辉认为新版《东方时空》与从前主持的《世界报道》样式没什么不同,只是表达方式有些改变。“新版《东方时空》是早间新闻,要求尽量活跃,讲话尽量轻松点,别老绷着。而《世界报道》在晚间播出,要求比较庄重一些。”
现在康辉“一点也不紧张了”。一个月下来,从台里部里的例会和观众通过各种渠道的反馈来看,康辉自称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其实,这是康辉在谦虚。从我了解的情况得知,康辉该是表现“最好的一个”才对。甚至有观众说,康辉的微笑,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带着一丝丝的暖意。有同事跟着起哄,“你干脆改名就叫‘丝丝暖意’吧。”康辉腼腆地笑了。
当记者问及康辉是如何完成由“播新闻”到“说新闻”的转变时,康辉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其实,我在主持《世界报道》时就一直在转变自己,丰富自己。后来,我播音已经比较注意口语化了,只是这个过程是平缓的,渐进的,可能你不能立马看出来,我的性格也是这样。我想,我只能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再说,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不同嘛。归根到底,无论“说”也好,“播”也罢,最重要的是传递信息,也不必把二者故意搞得泾渭分明。”
“成名与否,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重要。”康辉很认真地说,“你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达到了或自己认为满意就够了。”不过现在康辉的想法有了新的变化。“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否认,如果你有了一定的名气,再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更加便利,更加容易。否则,你努力了,别人也看不见。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我自己可以承受的情况下,我也还是希望我自己更有些名气。”
我知道,A型血的人特征之一就是追求完美。“你是A型血吗?”康辉微笑着点了点头。
|
|
|